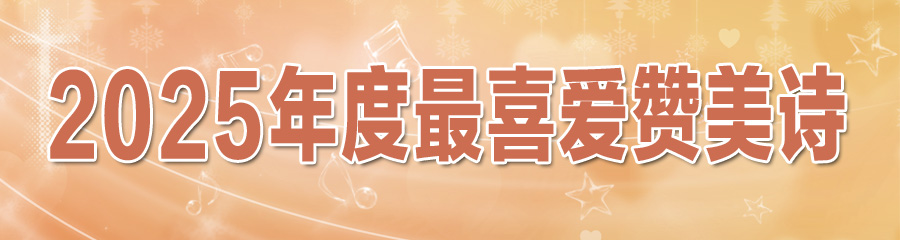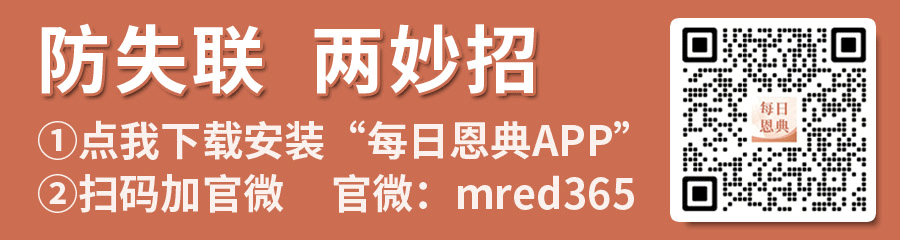早晨看《兄弟连》。讲到美军进入荷兰的爱因霍恩,刚巧遇到欢庆胜利的时刻,街头巷尾飘满了荷兰的国旗和那鲜亮的橙色旗帜,兴奋的人们走上街头,载歌载舞,姑娘们向着大兵献香吻。然而镜头一转,前一刻还在和某个中士缠绵的女郎,一下子被几个青年押到广场的某个角落,被迫跪着,一个女人动作麻利地剃光了那个女郎的头发。那个广场上已经押着好几个这样的女郎,有的神情漠然,有点啼哭不止。一个士兵问,她们到底做了什么?一个围观的男人鄙夷地答道:她们和德国人睡觉。她们运气算好的了,那些和德国人有往来的男人都被枪毙了。
大家都沉默了,也包括屏幕前的我。
在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里,我也看到过类似的一幕。战争结束,Melena被嫉妒愤怒的女人们给揪了出来……那一幕并未在我的理性中更多延展,战争的残酷性多少掩盖在一个女人的传奇底下。然而这一幕,却勾连起我的记忆和想象;而这偏偏发生在一个“胜利”的时刻,发生在柯丽•邓•波姆的荷兰。
柯丽在《密室》的最后一章里写道:“人们最难饶恕的倒不是德国人或日本人,却是曾经与敌人合作的荷兰同胞。我们时常在街上看见他们。他们的头被剃光了,眼中流露出畏缩的神情……他们被逐出家门之外,找不到工作,在街上受尽人们的讥笑和辱骂。”
然而,柯丽却收容了他们。战争时期,贝雅古屋是那些逃亡的犹太人的藏匿之地,战后又成为那些被弃的荷兰通敌者的容身之处。柯丽看顾他们,就像在那之前她看顾那些饱受战争创伤的同胞,或在那之后在德国看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样。
《密室》我已经读了三遍,但直到今天我看到电视里那激愤得几近狰狞的群众,我才那么迟钝地体会到,柯丽在战后所做的工作,比起她在战时所做的,可能更加地艰难,也更加重要。我并不是轻看柯丽一家人乃至那些“史密特先生”们的地下工作,我只是想说柯丽的身份绝不止于“女版的辛德勒”,《密室》的意义和地位也绝不等同于其他的二战纪实文学如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、《安妮日记》、《拉贝日记》。正如一个成长于1980-1990年代德国的商业经理说:“……通过电影、书本和历史老师,(我)有许多机会听闻关于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毁灭性的影响。尽管如此,柯丽•邓•波姆的《密室》从个人角度所展现的大屠杀的恐怖,使得人类所受到的痛苦尤为真实和个人化。文本强烈地传递了关于饶恕与和解的信息。就像作者教导我们的那样:即使在最糟糕的机遇中人们也能找到力量和希望。”
当柯丽回到故乡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无所事事之感,她尝试再做地下工作、做慈善工作,却换不得内心的平安。直到她想起姐姐碧西的异象,开始传讲她在牢狱之中所获得的信息,她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位置。她的饶恕,她的爱仇敌,是柯丽的故事的最高潮。
柯丽曾记载自己受邀去德国讲演的经历。在慕尼黑的一个教堂礼拜结束后,柯丽遇到了她在集中营里的一个狱卒。那个男人显然已经忘记了柯丽,满面笑容地上前表达他的感激,因为她的信息让他感到耶稣已经把他的罪洗干净了;于是,他伸出手来要和她相握。曾多次传讲饶恕的必要性的柯丽,这时却发现内里充满了愤怒和报复之心,于是她默祷着请求上帝饶恕自己的罪。当她终于能伸出手时,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。“从我的肩膀,沿着我的手臂,通过我的手心,有一股电流似乎从我身上传到他的身上,那时我心中涌起一股对这个陌生人强烈的爱,几乎把我完全淹没。”
也是在那一刻,柯丽才发现:“医治这世界的能力不系于我们自己的饶恕,也不系于自己的良善;乃系于神自己的饶恕和良善。当他吩咐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,跟着这命令而来的便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爱。”也是在这一刻,我才明白为什么说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器皿,是他的管道。我们本是一无所有的,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能盛装的,能传递的。而上帝通过柯丽所传递的信息就是:耶稣能够将失败转变为荣耀。
我曾经听过两个关于二战的故事,两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基本相同,大意是讲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,一个盟军士兵看到他的同伴们对德国战俘报复性地行私刑。第一个版本里的士兵看到人性的丑陋后,顿生“春秋无义战”之感,开始怀疑战争的公义性和人生的意义,越发质疑上帝的主权。而在另一个版本里,那个士兵也同样见识了人性的丑陋,感到人无法在他人和世间找到出路,而必须来到上帝面前……
第一个士兵的怀疑后来成了战后思潮的主流,哲学文学艺术集体陷入了一个“受苦时上帝在哪里”的约伯式的追问中。第二个士兵的声音相形之下却微弱得多;而且,即使我们在这个惨绝人寰的世道中能继续持守信仰,继续相信神是爱,但又如何能活出耶稣的教导和法则——去饶恕,去爱我们的仇敌呢?
我想到磕磕绊绊地追随耶稣基督的托尔斯泰,一生都陷入了一个自责性的反问中:为什么我不能实践我所信仰的?然而这个普通的钟表匠家庭,却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一页,共同演绎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教导我们的:谦逊,顺服,怜悯,一心服侍人,爱人如己,为朋友舍命,乃至爱我们的仇敌。
保罗说,没有义人,连一个也没有。然而,在《密室》的前言里,葛培里牧师将柯丽•邓•波姆与希伯来书中的那些信心伟人并列,称她为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人。正是她和她的家人那单纯无畏的信心,“为一个失落的世界,重新带来希望”。
写于2010.5
9月5日 每日恩典内容